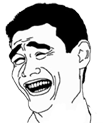复兴实验10届一班吧 关注:57贴子:15,198
- 12回复贴,共1页
1
青牛背上客,长笑过咸阳。
他记得那个侍读,姓颜名路,字无繇。那是嘉庆二十六年,那时他还年轻。相信这世道如同人们口耳相传的那样,总归是有正义,总归是凭正道。他带着一腔豪情热血随着那些中了举的同僚拜师行礼,但如今有些人已经不在,而那曾经的一腔热血换作了那官印下的朱砂,每一次按下,都压抑的胸膛隐隐作痛。
己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当年的张白圭变为了张首辅,而当年那个给予他提拔的徐阶也早就丧于田野,而当年那个总是温宛浅笑的年轻侍读,也己化为了一捧黄土。
门外风声竦竦,是要下雨了。
他想起也是那么一个天气,年轻的侍读泡的瓜片,青绿色的茶叶打着旋儿,嫩黄色的茶汤映着烛火,几个人起着哄的赖在府里不走,叨念着”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年轻侍读只是敛眉低笑,从黄梨木雕镂柜子里又拿出五六个骨瓷的茶杯。
他们当时年轻气盛,凤傲九洲,就连这喝茶听雨的文雅之事,谈及的也必定是将来的理想,也不知道是谁先问起的,问年轻的侍读有着怎样的抱负。
“我本青牛客,长笑过咸阳。”
一语既出,四下皆静。
“无繇,你…”坐在他旁边的张良蓦然开了口,“本不想…当官?”
年轻侍读提壶再次给他们茶杯灌入茶水,看见他们都瞪着自己,不禁笑出声来。
“只权当附庸风雅,当不得真。”
那笑容明艳太过美好,几乎骗过了所有人的眼睛,但骗不过张叔大,也没骗过坐在他身边的张良。
理由心生,象由心行。他挥手假装不经意碎了茶杯。白色瓷片四处散落在地上,易卦相叠,下巽上艮,事多变,是蛊卦。
三年之内必有大事生变。
他抬头看向颜路,年轻侍读冲他微微摇了摇头。
“倒是岁岁平安了,叔大。”张良出声说到,“不过彩头是讨了,这杯子你还是得赔师兄一个。”
他看得见张良眼中的了然,他比自己更懂得易卦之说。
命理难料,命数却已经定下。
“那是当然,日后必定赔给无繇。”
他说道,假装没看见张良眼中的绝望和心伤。
2
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
旋入雷渊,麋散而不可止些。
“大人,起风了,把窗子关了吧。”
“开着就好。”
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他不是暮年还无法效忠国家的文人騒客,他手握着整个明朝的命脉。可他也曾无力过,也曾尝过那一腔热血被冷雨浇透,冰的彻骨心寒。
那是他还年轻,那是他还是张叔大。
他瞧错了人,悟错了道。
严嵩开始下手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他将手伸入国子监。
刑不杀士大夫,更何况天子讲师。这怎么看也不像是个官场老手所干得事情。但是,他就是这样干了。
他先下手的,是颜路。
这在外人看来莫名其妙,而明理的来看,却不得不后背发凉。颜路是徐阶弟子,官至四品,但为人温润淡漠,党派之争中算不上有利的棋子,到要看的就是徐阶要不要这枚棋子。
若是徐阶要了,那便是公然接受了严嵩的挑战,但局势便会对自己不利。倘若是不要,昔日与颜路交好的官员便明白徐大人是怎样的人物,纷纷明哲保身,徐党便元气大伤。
这是步好棋。
徐阶没有做任何表态,只是吩咐人去张府把张夫人接来,又命人去跟着张良。
颜路与张良,徐阶明白的紧。
他就在一旁看着这一切。站在一旁,看着这是怎样的血雨腥风。看着自己怎样的无能为力。
波律香弥漫的到处都是,直直压进他的鼻腔。他看着张良跪在徐阶面前,曾经傲视一切的少年儿郎面带死灰,一字一啼血。
“求大人,救颜路。”
那六个字像是用张良所有的力气说道。他说完后就如同被抽了支架的布袋偶,头重重嗑在地上,四肢俯地。
四周寂静无声,只有窗外北风呼啸,如同冤人叫屈。
“并不是我不想救…只是为师也是无能为力啊!”
好个无能为力,好个只是为师!我敬你让我认清严嵩狗贼,我敬你忠信正义之士,到最后来发现你也是如此趋利附势,贪生怕死之辈!
但张叔大不能发话,因为趴在地上的张良没有说话,他甚至都没有动。
他看上去像死了一样。
许久,他听见张良说”学生明白。”声音平淡就如同他请教了徐阶一个简单问题。
他在徐阶眼里看到震惊和赞赏,他睁大眼睛不可置信的看向张良,他神色平常,一如往常那般随性淡漠模样。但,不,有一些东西徐阶没看到。
是张良从指尖滴落的鲜血。
一滴滴,像是颜府冬天的梅花。
何心隐说,王学兴衰与否,全靠张居正。
他是徐阶最宝贵的棋子。而颜路是徐阶最宝贵的弃子。
谁说命理不同?那些命理命数就如同拿在手里的蓍草,排列组合,全靠人心。
从一开始,便定了。回不去,改不了,变不通。
他觉的心寒又愤怒。
但他无能为力。
他还是认识些朋友,最终见到了颜路,血衣破败,遍体鳞伤。
但年轻侍读还是冲他宛尔一笑,瞧见他手中的食盒,轻声说道“怎着,想起我的杯子来了?”
“我倒是没有想到你和子房一样的小心眼。”他说道,声音哽咽。
“他还好吗?”
“是,还好。”他取出食盒里的饭菜,尽是药膳。
“叔大可曾带了纸笔过来?”颜路问道,看着摆在面前的饭菜,又叹了口气,“叔大,劳你…费心了…”
“纸笔我自是带了…只是无繇…你可…”你可拿的动笔?
翻滚的皮肉,红肿涨大的骨节,剥落的指甲,那双曾经映着绿茶宛如初春积雪般白皙的手,如今已经成了这番模样。
“不碍事的。”颜路说,“不碍事的。”
他递给他纸笔,牢房里烛火昏暗,一明一灭。他看着他一笔一划,写出那些字,它们亦如往昔那样隽永。
“请你替我…交给他。”
他收下,白纸染了血迹,零零散散,像是飘落在雪地的梅花。
他想起张良指尖留下的鲜血,没由的心疼了起来。
他想起自己新婚的妻子,她将他的头发和自己掺在一起,绾成了结,系在自己腰间配饰上。
生当结发,死当同穴。
同样都是情爱,同样都是至死不渝,却是如此巨大的差别。
“我定当亲手交给张良。”
颜路看向他,眉目仍是带着笑的,他说,“多谢。”
眸子亮如繁星。
他最终选择离去。
他写给徐阶这样一段话“古之匹夫尚有高论于天子之前者,今之宰相,竟不敢出一言,何则?!”
这就是他想说的了。
他看到最冰冷的人心,他看到最阴暗的官场,他看到这个貌似是有正道的世界其实是被无数血肉堆积而成,他看到昔日同僚如今化成一捧黄土。
这是他看到的。
他在曾经的贡院门口找到了张良。那人站在那里,目光不知盯向何处。
“他有东西给你。”
“……”
“你自己看吧。”
他将那张纸递了过去,张良恍如梦醒般,木讷接过。
那是首诗。
是《绸缪》。
“绸缪束薪,三星在天。
今夕何夕,见此良人。
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绸缪束刍,三星在隅。
今夕何夕,见此邂逅。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绸缪束楚,三星在户。
今夕何夕,见此粲者。
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今夕何夕,见此良人。
张良口中喷出鲜血染红了他穿的白布麻衣,大片的红色像极了那日他们去徐阶家谢师时门口大段红绸。
他想起那日发榜后的宴席,杯盏觥筹,张良高声唱的那一首《绸缪》,颜路微红的脸庞,以及那一声“你呀…”
那时候,这两人情根就已种下了吧。
他这么想着,背着行李一步一步走出城门,兀的又想起颜路的那一句“我本青牛客,长笑过咸阳。”
有人抓住了他的袍角,猛然把他从回忆中扯出来。
那是个老乞丐,求一块口粮。
他抬目四望,发现饿殍遍野。
3
伤哉生出瞿塘险,翻落黄粱一梦中。
这些都过了很久了。
他之后来了又回,他看着严嵩倒台,他看着徐阶败落,他看着高拱离去,他看着自己一路摇摇晃晃,风雨飘摇。
但他到时希望自己突然被惊醒,睁眼窗外春色正好,张良揪着他的鼻子一脸戏谑“白王八,再不醒就拿去炖汤啦!”
年轻侍读轻笑出声,继续低头弄琴。弹一曲《广陵散》。
但无人煮一锅黄梁。
窗外的雨大了起来,大风吹的他遍体生寒。
他伸手关了窗。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