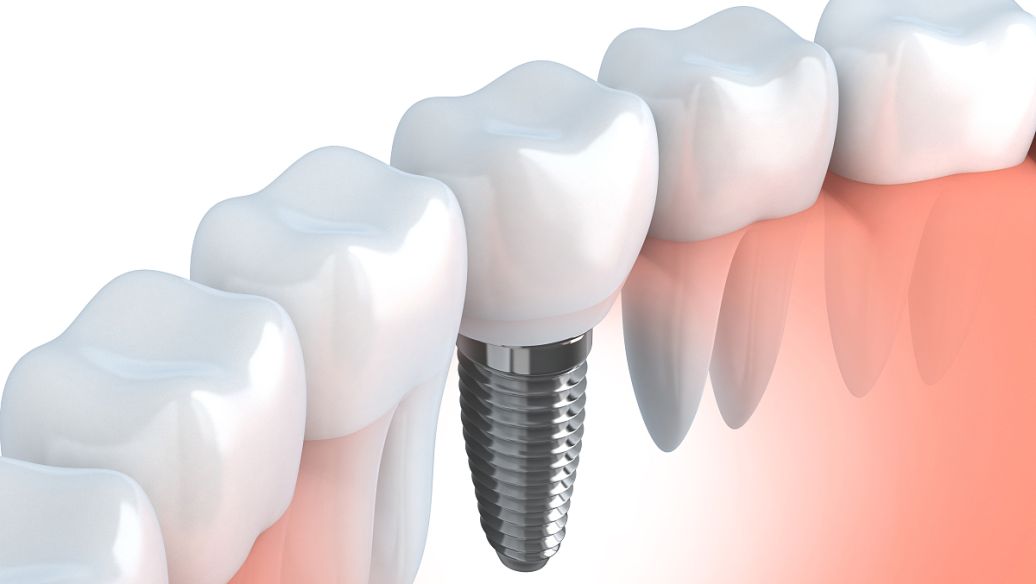莫福吧 关注:6,620贴子:42,834
小栗不在时的自戏1
终于又坐回到自己办公室的椅子上,面对着电脑单调而使人视觉器官不适的显示器,不自觉地锁紧了眉头。面前的工作列表上满满的都是前几天积压下来的单子——伦敦最主要的几个地下组织之间的关系最近微妙得紧,几乎每隔半小时就会有新的问题。苏格兰场最近也在这里微妙地插了一脚。虽然可能是那个人的意见。
注意到自己又忍不住回想起他——回想起这几天发生的事情,眉头皱的更紧了,无聊的工作。无趣,无趣,又是一成不变的满是死气的生活。皱着眉头,深深呼出一口气,微微眯了眯眼睛。慢慢向后倒去,深深陷在皮椅柔软的靠背里,两只手在面前合拢,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电脑,但根本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虽然这样混乱的局面也许是以前的自己所喜爱的,但那只是以前的自己!现在这东西看起来委实单调乏味。
注意到自己的动作——是那个人的习惯性动作——一下子把手放下,暗骂自己一声,着力从靠背上坐起来,但没能坚持多久又靠了回去。
窗外一直积着的闷云上终于划过一道闪亮的电迹,一下子被雷声从回忆中拖出,微微有点迷茫地望向窗外,看见窗户上映出自己熟悉又陌生的脸庞。
雨适时下了起来。暴雨。像是要用一粒又一粒的单调重新洗刷这个混乱肮脏鱼龙混杂的城市,洗刷形形色色人的野心和悲伤。站起来,走到窗前,俯视着窗前的马路。灯光在窗前的水珠上散成了一片。
正看着窗上自己的倒影,手机发出了短信提示音——那个人大声呼喊的“Boring”——左手摸摸口袋,掏出手机,是Moran。
“他走了。”
他还是走了。
抿着嘴看着发过来的模糊的照片。他带着那顶愚蠢的帽子,还有愚蠢的大衣,愚蠢的围巾,上了愚蠢的Mycraft的愚蠢的小黑车。
又是一条短信,他发过来的。
“我走了。”
狠狠按灭手机。
愚蠢的Sherlock,我知道。我一点也不想你。
终于又坐回到自己办公室的椅子上,面对着电脑单调而使人视觉器官不适的显示器,不自觉地锁紧了眉头。面前的工作列表上满满的都是前几天积压下来的单子——伦敦最主要的几个地下组织之间的关系最近微妙得紧,几乎每隔半小时就会有新的问题。苏格兰场最近也在这里微妙地插了一脚。虽然可能是那个人的意见。
注意到自己又忍不住回想起他——回想起这几天发生的事情,眉头皱的更紧了,无聊的工作。无趣,无趣,又是一成不变的满是死气的生活。皱着眉头,深深呼出一口气,微微眯了眯眼睛。慢慢向后倒去,深深陷在皮椅柔软的靠背里,两只手在面前合拢,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电脑,但根本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虽然这样混乱的局面也许是以前的自己所喜爱的,但那只是以前的自己!现在这东西看起来委实单调乏味。
注意到自己的动作——是那个人的习惯性动作——一下子把手放下,暗骂自己一声,着力从靠背上坐起来,但没能坚持多久又靠了回去。
窗外一直积着的闷云上终于划过一道闪亮的电迹,一下子被雷声从回忆中拖出,微微有点迷茫地望向窗外,看见窗户上映出自己熟悉又陌生的脸庞。
雨适时下了起来。暴雨。像是要用一粒又一粒的单调重新洗刷这个混乱肮脏鱼龙混杂的城市,洗刷形形色色人的野心和悲伤。站起来,走到窗前,俯视着窗前的马路。灯光在窗前的水珠上散成了一片。
正看着窗上自己的倒影,手机发出了短信提示音——那个人大声呼喊的“Boring”——左手摸摸口袋,掏出手机,是Moran。
“他走了。”
他还是走了。
抿着嘴看着发过来的模糊的照片。他带着那顶愚蠢的帽子,还有愚蠢的大衣,愚蠢的围巾,上了愚蠢的Mycraft的愚蠢的小黑车。
又是一条短信,他发过来的。
“我走了。”
狠狠按灭手机。
愚蠢的Sherlock,我知道。我一点也不想你。
小栗不在时的自戏3
银行楼顶上的风好大。
带着墨镜依旧微微眯眼,坐在边缘俯视底下繁华而有序的街道上面的人进进出出。
可悲。忍不住微微扬起一边的嘴角。
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于是就开开心心地,不自觉的被社会所操纵,被和平所俘获,沉浸在甜腻腻的一成不变里,却看不见社会这个热带水果是因为腐烂才发出醉人的酒香。
该结束了。
微微扬起头,露出陶醉的笑容,两只手像个指挥家一样抬起。
伦敦,听听我演奏的音乐,然后,醒来吧!
笑容一下子收敛,手陡然下挥,下面的地面上整齐地响起一排枪声,接着就是不出意外的对这音乐的赞美声——混乱,爆炸,人群的嘈杂声。世界一下子有了色彩。
楼顶上听着音乐的指挥家的手又狂乱而没有章法地挥舞起来,不,不是没有章法,混乱就是一种章法。
“Seb,你猜猜今天苏格兰场多久会到?”
“10分钟,也许更多,Sir。”
10分钟,正好演奏完巴赫一支舞曲的第一部分。
“那就,继续吧。”
银行楼顶上的风好大。
带着墨镜依旧微微眯眼,坐在边缘俯视底下繁华而有序的街道上面的人进进出出。
可悲。忍不住微微扬起一边的嘴角。
以为自己是自由的,于是就开开心心地,不自觉的被社会所操纵,被和平所俘获,沉浸在甜腻腻的一成不变里,却看不见社会这个热带水果是因为腐烂才发出醉人的酒香。
该结束了。
微微扬起头,露出陶醉的笑容,两只手像个指挥家一样抬起。
伦敦,听听我演奏的音乐,然后,醒来吧!
笑容一下子收敛,手陡然下挥,下面的地面上整齐地响起一排枪声,接着就是不出意外的对这音乐的赞美声——混乱,爆炸,人群的嘈杂声。世界一下子有了色彩。
楼顶上听着音乐的指挥家的手又狂乱而没有章法地挥舞起来,不,不是没有章法,混乱就是一种章法。
“Seb,你猜猜今天苏格兰场多久会到?”
“10分钟,也许更多,Sir。”
10分钟,正好演奏完巴赫一支舞曲的第一部分。
“那就,继续吧。”
小栗不在时的自戏9
杀了他。
对,稳稳拿起你手中的枪,探长。
看看你面前的那张嘴脸。冷漠,嘲讽,恶心。看看那该死的恶心的自高自大的笑容,探长,我亲爱的雷斯垂德。那是怎样的令人恶心。那是混迹政坛多少年才留下的恶趣味。
他在玩弄你,探长。
再怎么迟钝你也应该发现了。
看看他惹人生厌的黑色雨伞,一副被权力牢牢控制了内心的空虚样子。他不过是和他弟弟一样的吸毒者。探长。他们都没有道德伦理,有的只是有趣与没趣的事情的分别。你早该知道的。但是现在一点不迟。
你看看,我们现在,你我都热爱的伦敦就是这样一点点被这对兄弟玩弄至支离破碎,只有你,只有他已经因为你的迟钝与愚忠放松了的你,才有这个能力与资格做出这件伟大的事情。
不用担心后果,作为我的老朋友我当然愿意免费帮你扫尾,亲爱的雷斯垂德。
开枪吧。
杀了他。
然后告诉我你爱伦敦。
杀了他。
对,稳稳拿起你手中的枪,探长。
看看你面前的那张嘴脸。冷漠,嘲讽,恶心。看看那该死的恶心的自高自大的笑容,探长,我亲爱的雷斯垂德。那是怎样的令人恶心。那是混迹政坛多少年才留下的恶趣味。
他在玩弄你,探长。
再怎么迟钝你也应该发现了。
看看他惹人生厌的黑色雨伞,一副被权力牢牢控制了内心的空虚样子。他不过是和他弟弟一样的吸毒者。探长。他们都没有道德伦理,有的只是有趣与没趣的事情的分别。你早该知道的。但是现在一点不迟。
你看看,我们现在,你我都热爱的伦敦就是这样一点点被这对兄弟玩弄至支离破碎,只有你,只有他已经因为你的迟钝与愚忠放松了的你,才有这个能力与资格做出这件伟大的事情。
不用担心后果,作为我的老朋友我当然愿意免费帮你扫尾,亲爱的雷斯垂德。
开枪吧。
杀了他。
然后告诉我你爱伦敦。
小栗不在时的自戏11
If the day is done ,
If birds sing no more .
If the wind has fiagged tired ,
Then draw the veil of darkness thick upon me ,
Even as thou hast wrapt the earth with
The coverlet of sleep and tenderly closed ,
The petals of the drooping lotus at dusk.
垂眸舔舐金属。因为其表面的黑色漆而没有尝到血的腥甜。但是没有因此失望,因为自己的口中即将溢满这不再名为生命的液体。
金属划过柔软的舌头给人一种淡淡的反胃感,是硝烟和血,还是冰冷和死亡?这种已经知道结局的东西总是勾不起自己的兴趣,想起以前陪Molly去看的电影,只是在小姑娘与小狗玩耍的时候尽量微笑,Molly倒是委实开心,不停晃动自己的手臂。但是她总是不知道,喜剧是为了最后的悲剧,只有毁掉人们以之为珍贵的东西,这个虚假的人类造物才称得上是好的悲剧。毁掉的越珍贵,他就越成功,这不过是一个套路。所以最后小狗死了,小姑娘孤独了,Molly哭了。自己只是冷漠地吃着爆米花,无喜无悲。
死亡?死亡是什么?无边无际的寂寞与让人恶心的平静。不再是和世界一样的腐烂而有光鲜的表面,而是永远的沉没。我厌恶自己的死亡,但是我现在才知道我对他的渴求——如果死亡就可以让自己最后对于社会的呼喊完美谢幕。
他没有死。所以我也没有死。
不知道是世界对我的报复还是希望我完成一切的奖励,我现在没有死。
I should sing with my husky throat?
The land which is being hitted by the storm?
The river which is always filled with our indignation?
The wind which blows violently forever?
And the most tenderness dawn which comes from the forest.
世界会后悔。
世界一定会后悔放跑了我这样的挣扎者。
我将永远在此,作为最后一个恶魔,最后一个清醒的人,奏鸣最理智的疯狂的卡农。
枪鸣。
倒地。
微笑。
If the day is done ,
If birds sing no more .
If the wind has fiagged tired ,
Then draw the veil of darkness thick upon me ,
Even as thou hast wrapt the earth with
The coverlet of sleep and tenderly closed ,
The petals of the drooping lotus at dusk.
垂眸舔舐金属。因为其表面的黑色漆而没有尝到血的腥甜。但是没有因此失望,因为自己的口中即将溢满这不再名为生命的液体。
金属划过柔软的舌头给人一种淡淡的反胃感,是硝烟和血,还是冰冷和死亡?这种已经知道结局的东西总是勾不起自己的兴趣,想起以前陪Molly去看的电影,只是在小姑娘与小狗玩耍的时候尽量微笑,Molly倒是委实开心,不停晃动自己的手臂。但是她总是不知道,喜剧是为了最后的悲剧,只有毁掉人们以之为珍贵的东西,这个虚假的人类造物才称得上是好的悲剧。毁掉的越珍贵,他就越成功,这不过是一个套路。所以最后小狗死了,小姑娘孤独了,Molly哭了。自己只是冷漠地吃着爆米花,无喜无悲。
死亡?死亡是什么?无边无际的寂寞与让人恶心的平静。不再是和世界一样的腐烂而有光鲜的表面,而是永远的沉没。我厌恶自己的死亡,但是我现在才知道我对他的渴求——如果死亡就可以让自己最后对于社会的呼喊完美谢幕。
他没有死。所以我也没有死。
不知道是世界对我的报复还是希望我完成一切的奖励,我现在没有死。
I should sing with my husky throat?
The land which is being hitted by the storm?
The river which is always filled with our indignation?
The wind which blows violently forever?
And the most tenderness dawn which comes from the forest.
世界会后悔。
世界一定会后悔放跑了我这样的挣扎者。
我将永远在此,作为最后一个恶魔,最后一个清醒的人,奏鸣最理智的疯狂的卡农。
枪鸣。
倒地。
微笑。
小栗不在时的自戏12
慢慢扶着桌面起身,绕过桌子弯腰拾起掉在办公桌前地面上的刀子。
指腹微微划过刀片的侧面,一面感受刀子上尚留的温度,一面马上沾满了半凝固的暗红的血。于是微微垂眸看向地面,纷乱的血迹沿着手工皮鞋底下的花纹流出一个符号。边上留着一根手指。
恶心。
微微皱起眼睛下面的肌肉,嫌恶地俯视那个愚蠢的遗留物,像是某个漂亮的华丽的天天对着圣母玛利亚高唱赞歌的18世纪的基督教教堂大厅中心地面上出现了一个湿润的保险套一样令人恶心。想起那个早就知道自己结局的人恶心地哭诉,咒骂,绝望地跪倒的样子。神明?忍不住嗤笑,就算有神明,也必然是一个喜欢看你们祈求,绝望地跪倒最后迎接必然的死亡的家伙。不然为何死亡这般美妙的东西却有着这样一个令这些愚蠢的家伙看不清其本质的序幕?宏大如同百人唱诗一般令人震耳欲聋,于是只知道赞美神明,而看不见自己的可鄙。
于是不再低头去看那个恶心的遗留物,反正一会总是有人会来清理的。
步伐轻快划过钢琴面前,在白色的大理石地面上做出一个华丽的旋转,然后向看不见的观众深深鞠躬,表情高傲平静,伸出沾了鲜血的手指轻轻划过黑白的音符。世人尽可言语。我自风中起舞。
Hold infining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ng in an hour.
手指轻轻按出一个单调轻快的节奏。
微微侧头闭眼似乎等待什么东西来应和。
于是再次睁眼又一次准确按出刚刚那个即兴的节奏,依旧闭眼侧头倾听。
我们的艺术家终于露出满意的笑容,于是夸张地旋身坐下,左手再次按出那个旋律,但是并未停留,开始后准确的几秒右手去和了,按出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旋律,紧接着是第三遍,第四遍,同样的单调的旋律如同海潮一般自地面下巨大的水中由裂缝里涌出,于是一发不可收拾,狂潮一般在名为情绪的巨风中一波又一波打在世界的崖壁上,击打出名为反抗的怒吼。
这是最理智的演奏方式,以几乎是机械一般的精准一遍又一遍微妙地重复同一个节奏于是击打出最夸张的情感。
卡农一曲毕,钢琴家陡然起身出门,大有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之势。
慢慢扶着桌面起身,绕过桌子弯腰拾起掉在办公桌前地面上的刀子。
指腹微微划过刀片的侧面,一面感受刀子上尚留的温度,一面马上沾满了半凝固的暗红的血。于是微微垂眸看向地面,纷乱的血迹沿着手工皮鞋底下的花纹流出一个符号。边上留着一根手指。
恶心。
微微皱起眼睛下面的肌肉,嫌恶地俯视那个愚蠢的遗留物,像是某个漂亮的华丽的天天对着圣母玛利亚高唱赞歌的18世纪的基督教教堂大厅中心地面上出现了一个湿润的保险套一样令人恶心。想起那个早就知道自己结局的人恶心地哭诉,咒骂,绝望地跪倒的样子。神明?忍不住嗤笑,就算有神明,也必然是一个喜欢看你们祈求,绝望地跪倒最后迎接必然的死亡的家伙。不然为何死亡这般美妙的东西却有着这样一个令这些愚蠢的家伙看不清其本质的序幕?宏大如同百人唱诗一般令人震耳欲聋,于是只知道赞美神明,而看不见自己的可鄙。
于是不再低头去看那个恶心的遗留物,反正一会总是有人会来清理的。
步伐轻快划过钢琴面前,在白色的大理石地面上做出一个华丽的旋转,然后向看不见的观众深深鞠躬,表情高傲平静,伸出沾了鲜血的手指轻轻划过黑白的音符。世人尽可言语。我自风中起舞。
Hold infining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ng in an hour.
手指轻轻按出一个单调轻快的节奏。
微微侧头闭眼似乎等待什么东西来应和。
于是再次睁眼又一次准确按出刚刚那个即兴的节奏,依旧闭眼侧头倾听。
我们的艺术家终于露出满意的笑容,于是夸张地旋身坐下,左手再次按出那个旋律,但是并未停留,开始后准确的几秒右手去和了,按出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旋律,紧接着是第三遍,第四遍,同样的单调的旋律如同海潮一般自地面下巨大的水中由裂缝里涌出,于是一发不可收拾,狂潮一般在名为情绪的巨风中一波又一波打在世界的崖壁上,击打出名为反抗的怒吼。
这是最理智的演奏方式,以几乎是机械一般的精准一遍又一遍微妙地重复同一个节奏于是击打出最夸张的情感。
卡农一曲毕,钢琴家陡然起身出门,大有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之势。
我早该预见自己的死亡——就像某个人说的:蛋糕总是有奶油的一面着地一样——世界总是不会让我完美谢幕。
看看,死了就是死了,死了世界还是世界,甚至伦敦还是伦敦,Sherlock还是Sherlock。只有Moriarty不再是Moriarty。多么失败的人生!除了这一辈某些被我照顾过的人,下一辈可能会知道我的人几乎已经是屈指可数了。看看,世界花了多少时间就把我消磨殆尽。
那还不如死亡。
这是一个悖论。
我总是喜欢黑暗,当我端坐在陌客的怀抱里我总是有安全感以及一种莫名的平静。我曾经一次又一次告诉我的老友我的构想,我的经历,我的成功以及那一个个甜美又让人无奈的失败。
我在黑暗里面慢慢进到我的思维宫殿里面,以缓慢的速度把自己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化作一个个绝望当中的不那么绝望的装饰品,然后一遍又一遍抚摸,确认,亲吻。像一个怀旧恋物的疯子,又像一个挫败绝望的傻瓜。
well,其实的确如此。
来啊,开枪啊,我的一切也不过是和马格努森一样装在这个不大的扁瓜一样的东西里面,就算他的背后是怎么样怎么样巨大的殿堂,现在在这里的具象化也不过是一个一枪就可以结束的脆弱的东西。就像挂住衣服的弯钩,没有它衣服就会顺理成章地落地。
现在,开枪吧亲爱的。开枪换来的是一个你们所期待的和平的伦敦,最后一个随机变量将被你们抹去,于是你们收获一个循环往复的可爱的伦敦——well,your Lundon.
不要犹豫,我将死亡,不管是必将还是马上,我将死亡,我将告别伦敦,告别这个一面造就我一面毁灭我的世界,不再做他的奴仆,走向你们达不到的自由的境地。
再见,伦敦。反正没有人会祭奠。
再见,亲爱的人们,反正你们永远不希望再见。
再见,世界,你这该死的,性感的,让人无可奈何依旧投奔怀抱的——爱人。
well,再见。
看看,死了就是死了,死了世界还是世界,甚至伦敦还是伦敦,Sherlock还是Sherlock。只有Moriarty不再是Moriarty。多么失败的人生!除了这一辈某些被我照顾过的人,下一辈可能会知道我的人几乎已经是屈指可数了。看看,世界花了多少时间就把我消磨殆尽。
那还不如死亡。
这是一个悖论。
我总是喜欢黑暗,当我端坐在陌客的怀抱里我总是有安全感以及一种莫名的平静。我曾经一次又一次告诉我的老友我的构想,我的经历,我的成功以及那一个个甜美又让人无奈的失败。
我在黑暗里面慢慢进到我的思维宫殿里面,以缓慢的速度把自己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化作一个个绝望当中的不那么绝望的装饰品,然后一遍又一遍抚摸,确认,亲吻。像一个怀旧恋物的疯子,又像一个挫败绝望的傻瓜。
well,其实的确如此。
来啊,开枪啊,我的一切也不过是和马格努森一样装在这个不大的扁瓜一样的东西里面,就算他的背后是怎么样怎么样巨大的殿堂,现在在这里的具象化也不过是一个一枪就可以结束的脆弱的东西。就像挂住衣服的弯钩,没有它衣服就会顺理成章地落地。
现在,开枪吧亲爱的。开枪换来的是一个你们所期待的和平的伦敦,最后一个随机变量将被你们抹去,于是你们收获一个循环往复的可爱的伦敦——well,your Lundon.
不要犹豫,我将死亡,不管是必将还是马上,我将死亡,我将告别伦敦,告别这个一面造就我一面毁灭我的世界,不再做他的奴仆,走向你们达不到的自由的境地。
再见,伦敦。反正没有人会祭奠。
再见,亲爱的人们,反正你们永远不希望再见。
再见,世界,你这该死的,性感的,让人无可奈何依旧投奔怀抱的——爱人。
well,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