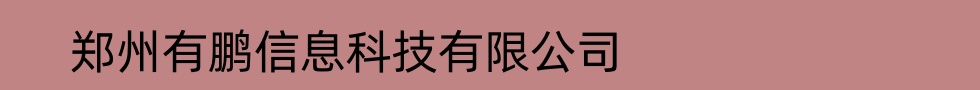世上最美的潜水者
那个尴尬的傻子死了,人们才发现他美得惊心动魄。
——加西亚·马尔克斯
1
大雨连月不止。黑色的云长久地排徊在城市上空,间或有短暂的放晴,走出屋外的人们得以享受晚霞或晨光的蔽阴,那时候的雨是潜伏在暗处的晚香玉,时刻准备着在下一个时间循环里从天而落,重现滂沱。它像整个降落的细碎天空,带着阴郁又温柔的梦网,用纤长的玻璃丝线把整个世界变成晶莹剔透的水晶立方体、一座迷幻的温室花房,在融化的水泥和24小时营业的灯光里,时间发芽疯长。
多年以后,当古明地恋回想随军的这段日子时,她竟然无法将二线战地的场景从雨后混杂着医用酒精气味的湿热空气和怀旧情绪中剥离。那时的她其实见惯了血但还远没有见惯铁,她对一线战场的了解只在射命丸文日日夜夜在打字机上撰写的文字中,伤员身上、心上那些惨不忍睹的伤口里,以及藤原妹红竭力为她描述的画面里。这部分是由于她从未真正克服对战争的恐惧,部分是由于战争中真正发生的事都是最高军事机密。她难以理解全身遍布伤痕和淤青的藤原妹红是怎么活下来的,而勒痕和义肢更是她不能想象的;她敢说这些才是让藤原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真正原因,但她不会点破,因为这决不是一个二线随军医生有资格知道的事。
在那个大雨滂沱不止的日子里,藤原妹红躺在简易担架上满身泥泞地被送过来时,古明地恋和射命丸文都万万料不到是她。当时已经是夜里,护士急促地拍着门,古明地医生,她说,古明地医生,刚刚送进来一个少校。恋急匆匆地披上外衣走出门去,看见几个护士正把一个简易担架抬进走廊另一端的病房里,凄厉可怖的叫声从护士服中间传出来。
古明地恋皱了皱眉,决定先去其他病房里巡视一圈,尖叫声会惊扰伤病员,更不用说只有那个人镇定下来之后她才能去给他或她看病。在走廊里她听见几个医生在窃窃私语,聊的好像就是刚送进来的那个少校,据说是位2040年左右入伍的女军人,但长期存在反战情绪;把她送来似乎并不是为了治愈她,而更像是抛弃变质的弃子。古明地恋摇摇头,她本想之后去问问射命丸文,但后来她想起这些不是可以透露给战地记者的事情。她们一无所知。
依次安抚完其他人后她才踏进那间病房。行军床上的人在镇静药物和军人素质的双重作用下已经趋于冷静。护士们清洗过的脸庞轮廓显出女性特征,古明地恋回想起之前那凄厉沙哑、辨不出性别的叫声。她的长相让恋感到有些熟悉,但又想不起来是谁,只是触动了恋心里一些甜美的、回不去的过往。她直直地注视着恋。
“医生,我会死的吧。”
“我们都会。”
那就是藤原妹红。那之后的事情被大脑的自动保护机制删除,她不记得自己怎样确认了她的身份、又是怎么回到宿处的,更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在抽泣、寒冷和复杂情感交替的汹涌之间入睡的;她在恍惚中想起还住在幻想乡的时候,姐姐陪她读诗集时读到的一句话:“你看不见,也听不见,这却是好的。”随即她发觉自己醒了,七窍和声带早已粘连在一起,而窗外黎明的灰色长手指正牢牢抓住变得黯淡的星星;以及,她在睡眠那冰冷的怀抱里莫名其妙地哭泣,想得更多的竟然是古明地觉和博丽灵梦,而不是藤原妹红。
她想起幻想出以后在藤原妹红的酒吧打工的日子,其实她本想写小说,可惜没有半点起色;和她一起离开的射命丸文大概还在什么媒体公司手下日夜劳碌奔波,她则几乎已经放弃人生在文家里做了家里蹲。
古往今来有无数案例告诉我们,绝不能轻易地把任何一位艺术家武断地判定为所谓家里蹲;万一某一天他们在苦心孤诣伏案创作时突然猝死当场,第二天他们的名字就能从被嘲笑的潜水者变成耀眼的艺术新星,被整个艺术界捧上天,如果属于不幸的英年早逝可能还有加持效果。更何况古明地恋还有一位优秀的作家长姐古明地觉,用笔名写着摄人心魄的海浪般的文字,比目前的古明地恋强了不知多少倍;她的文字只面向自己,除了把自己封锁在一方天地里之外亳无价值。
那个尴尬的傻子死了,人们才发现他美得惊心动魄。
——加西亚·马尔克斯
1
大雨连月不止。黑色的云长久地排徊在城市上空,间或有短暂的放晴,走出屋外的人们得以享受晚霞或晨光的蔽阴,那时候的雨是潜伏在暗处的晚香玉,时刻准备着在下一个时间循环里从天而落,重现滂沱。它像整个降落的细碎天空,带着阴郁又温柔的梦网,用纤长的玻璃丝线把整个世界变成晶莹剔透的水晶立方体、一座迷幻的温室花房,在融化的水泥和24小时营业的灯光里,时间发芽疯长。
多年以后,当古明地恋回想随军的这段日子时,她竟然无法将二线战地的场景从雨后混杂着医用酒精气味的湿热空气和怀旧情绪中剥离。那时的她其实见惯了血但还远没有见惯铁,她对一线战场的了解只在射命丸文日日夜夜在打字机上撰写的文字中,伤员身上、心上那些惨不忍睹的伤口里,以及藤原妹红竭力为她描述的画面里。这部分是由于她从未真正克服对战争的恐惧,部分是由于战争中真正发生的事都是最高军事机密。她难以理解全身遍布伤痕和淤青的藤原妹红是怎么活下来的,而勒痕和义肢更是她不能想象的;她敢说这些才是让藤原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真正原因,但她不会点破,因为这决不是一个二线随军医生有资格知道的事。
在那个大雨滂沱不止的日子里,藤原妹红躺在简易担架上满身泥泞地被送过来时,古明地恋和射命丸文都万万料不到是她。当时已经是夜里,护士急促地拍着门,古明地医生,她说,古明地医生,刚刚送进来一个少校。恋急匆匆地披上外衣走出门去,看见几个护士正把一个简易担架抬进走廊另一端的病房里,凄厉可怖的叫声从护士服中间传出来。
古明地恋皱了皱眉,决定先去其他病房里巡视一圈,尖叫声会惊扰伤病员,更不用说只有那个人镇定下来之后她才能去给他或她看病。在走廊里她听见几个医生在窃窃私语,聊的好像就是刚送进来的那个少校,据说是位2040年左右入伍的女军人,但长期存在反战情绪;把她送来似乎并不是为了治愈她,而更像是抛弃变质的弃子。古明地恋摇摇头,她本想之后去问问射命丸文,但后来她想起这些不是可以透露给战地记者的事情。她们一无所知。
依次安抚完其他人后她才踏进那间病房。行军床上的人在镇静药物和军人素质的双重作用下已经趋于冷静。护士们清洗过的脸庞轮廓显出女性特征,古明地恋回想起之前那凄厉沙哑、辨不出性别的叫声。她的长相让恋感到有些熟悉,但又想不起来是谁,只是触动了恋心里一些甜美的、回不去的过往。她直直地注视着恋。
“医生,我会死的吧。”
“我们都会。”
那就是藤原妹红。那之后的事情被大脑的自动保护机制删除,她不记得自己怎样确认了她的身份、又是怎么回到宿处的,更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在抽泣、寒冷和复杂情感交替的汹涌之间入睡的;她在恍惚中想起还住在幻想乡的时候,姐姐陪她读诗集时读到的一句话:“你看不见,也听不见,这却是好的。”随即她发觉自己醒了,七窍和声带早已粘连在一起,而窗外黎明的灰色长手指正牢牢抓住变得黯淡的星星;以及,她在睡眠那冰冷的怀抱里莫名其妙地哭泣,想得更多的竟然是古明地觉和博丽灵梦,而不是藤原妹红。
她想起幻想出以后在藤原妹红的酒吧打工的日子,其实她本想写小说,可惜没有半点起色;和她一起离开的射命丸文大概还在什么媒体公司手下日夜劳碌奔波,她则几乎已经放弃人生在文家里做了家里蹲。
古往今来有无数案例告诉我们,绝不能轻易地把任何一位艺术家武断地判定为所谓家里蹲;万一某一天他们在苦心孤诣伏案创作时突然猝死当场,第二天他们的名字就能从被嘲笑的潜水者变成耀眼的艺术新星,被整个艺术界捧上天,如果属于不幸的英年早逝可能还有加持效果。更何况古明地恋还有一位优秀的作家长姐古明地觉,用笔名写着摄人心魄的海浪般的文字,比目前的古明地恋强了不知多少倍;她的文字只面向自己,除了把自己封锁在一方天地里之外亳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