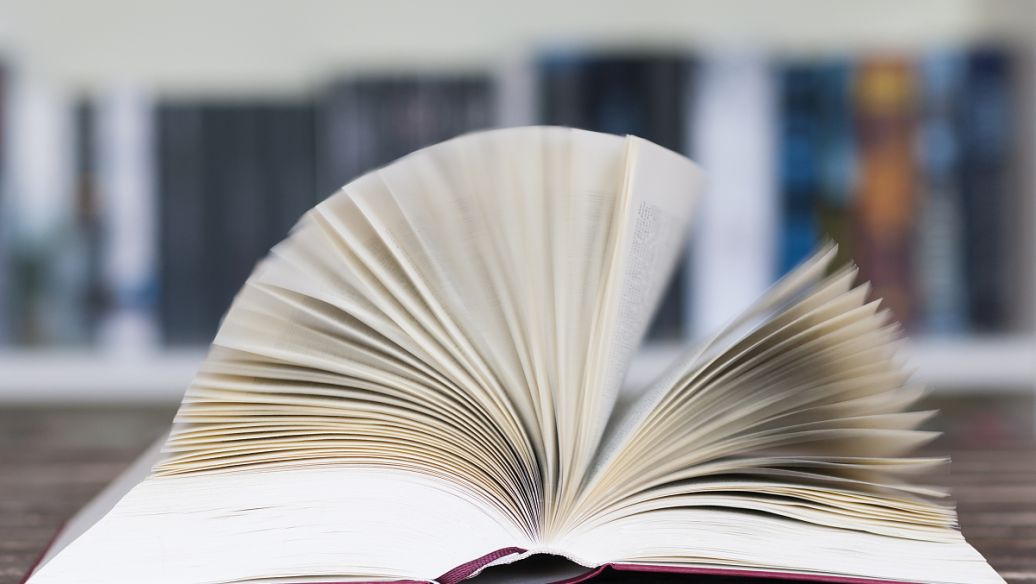文学吧 关注:1,194,439贴子:8,764,918
- 14回复贴,共1页
虚无主义就是一切都没意义,当然这是事实,人周围社会的一切都是非自然,被构建的,如果讨论私有制,讨论资产阶级法权导向的应试教育,讨论如此衍生的消费主义,商品符号,毫无疑问更让人更沮丧,不禁让人发问“我周围的一切都是被塑造的,连人生的目的都是他人强加给我的,我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而存在主义只在虚无主义的基础上加了一条讨论便逆转了这种阴暗,那就是人存在的意义是由自己创造的,人生没有意义,这种绝对的虚无意味着绝对的(意志)自由,你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权在每个人自己,而且必须要回答。“我们必须假设,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向山顶推着石头可怜吗?难道活着就不可怜吗?可是为什么可怜呢?可怜吗?不可怜吗?幸福吗?我们必须假设自己是幸福的,哪怕我们所做的一切在宇宙的尺度下是荒谬的,可我就是要做,而不是谁施加于我。
加缪的话,就是“荒诞——反抗”体系了呗,世界是荒诞的,人生本身也是没有意义的,所谓“生而必死,劳而无功”,只能是通过接连不断的选择进行反抗来赋予人生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有一个大的目标,加缪早期的作品《快乐的死》中的主角的目标就是让自己快乐,以此战胜了世间的寂寞和对死亡的恐惧,可以说是人在自己身上创造命运的尝试,当然,他有的是时间和金钱,这个条件是奢侈的。
因此必须注意,没有一个稳定的状态,因果和非因果是混淆不清的,有些时候事情就是那么发生,也说不出什么道理。在《卡利古拉》里,卡利古拉从暴君变成了一个存在主义者的形象,他“换上神的那副愚蠢又不可理解的面貌”亲自告诉了自己的国民这个世界可以有多荒唐:贵族可以突然变成被奴役羞辱的人,一个打扮得相当滑稽的男人会自称维纳斯让人民起誓下跪,一个人在战争和瘟疫之外可以随意地死掉,这些都没什么道理。他本人则坚持对抗荒诞,这在两个做法上特别突出,一个是他坚持使用逻辑推理的形式,尽管其结果可能是错误的,第二个则是“得到月亮”,也就是完成不可能的事,总体来看就是通过暴君式的权力使人能够在形式和结果上打破旧有模式(世界的圈套),他的存在由此在暴君外有了思想家的意义,即是让人活在真实之中。对他来说,人无力也无心改变突如其来的不幸、突如其来的死,这种生活就是恶心的,是虚无。他对虚无的对抗表现得相当宏大,包含着死和罪孽,人反抗虚无、反抗荒诞所付出的代价和痛苦可以是很夸张的。人也可以不反抗,结果可能是成为行尸走肉或者自杀,但是这种放弃之前往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被放逐不等于堕入虚无。像《局外人》里的默尔索,我不会认为他被虚无打败了,只会认为他是被别人的虚无给虚无化了,关键在于他有一个关于自我的标准,也就是他说的“我对自己有把握”,他对幸福有自己的理解,虽然对外界的情感回应少,但是自己能认为这种生活是“值得过”的。所以除了《戒严》里那种坚定的意志之外,必须看到“我”的存在。而前面又提到,反抗的过程中,选择是频繁的,“自由选择”中的“自由”成为了一种痛苦,因此在终极目标之间必须存在一种具体的东西,否则人支撑不住。在《鼠疫》里可以经常看到“抽象概念”这个词,拿里面出现的比较多的“爱”这个字来举例,没有博爱一类的强调,最多的是具体的男女之情,此外就是几个医生和志愿者之间的交心,人是通过这些度过看不到头的瘟疫和禁闭。虚无也不是说有就有说没就没的,有的人因为恐惧虚无沉迷感官刺激,因为堕入虚无就不再感受到虚无的侵袭,同时可能在这之后出现禁欲的想法,想以秩序来对抗虚无;有的人因为恐惧虚无而产生自恋,试图把自己当作悲剧主角以感受到忧郁和虚无的美,或是因此产生恋尸或恋童的倾向,以感受自身的生命力或是他们的纯真。对虚无的感受由此可能是不真切的,认为自己和虚无言和的人可能正在挣扎,或是相反的情况,克服虚无只能是在心中不断建立栖息地,中间任何一个时点的意义都有可能被推翻。就像楼上说的,西西弗斯推石头确实是很好的例子,必须认为他是幸福的。
因此必须注意,没有一个稳定的状态,因果和非因果是混淆不清的,有些时候事情就是那么发生,也说不出什么道理。在《卡利古拉》里,卡利古拉从暴君变成了一个存在主义者的形象,他“换上神的那副愚蠢又不可理解的面貌”亲自告诉了自己的国民这个世界可以有多荒唐:贵族可以突然变成被奴役羞辱的人,一个打扮得相当滑稽的男人会自称维纳斯让人民起誓下跪,一个人在战争和瘟疫之外可以随意地死掉,这些都没什么道理。他本人则坚持对抗荒诞,这在两个做法上特别突出,一个是他坚持使用逻辑推理的形式,尽管其结果可能是错误的,第二个则是“得到月亮”,也就是完成不可能的事,总体来看就是通过暴君式的权力使人能够在形式和结果上打破旧有模式(世界的圈套),他的存在由此在暴君外有了思想家的意义,即是让人活在真实之中。对他来说,人无力也无心改变突如其来的不幸、突如其来的死,这种生活就是恶心的,是虚无。他对虚无的对抗表现得相当宏大,包含着死和罪孽,人反抗虚无、反抗荒诞所付出的代价和痛苦可以是很夸张的。人也可以不反抗,结果可能是成为行尸走肉或者自杀,但是这种放弃之前往往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过程,被放逐不等于堕入虚无。像《局外人》里的默尔索,我不会认为他被虚无打败了,只会认为他是被别人的虚无给虚无化了,关键在于他有一个关于自我的标准,也就是他说的“我对自己有把握”,他对幸福有自己的理解,虽然对外界的情感回应少,但是自己能认为这种生活是“值得过”的。所以除了《戒严》里那种坚定的意志之外,必须看到“我”的存在。而前面又提到,反抗的过程中,选择是频繁的,“自由选择”中的“自由”成为了一种痛苦,因此在终极目标之间必须存在一种具体的东西,否则人支撑不住。在《鼠疫》里可以经常看到“抽象概念”这个词,拿里面出现的比较多的“爱”这个字来举例,没有博爱一类的强调,最多的是具体的男女之情,此外就是几个医生和志愿者之间的交心,人是通过这些度过看不到头的瘟疫和禁闭。虚无也不是说有就有说没就没的,有的人因为恐惧虚无沉迷感官刺激,因为堕入虚无就不再感受到虚无的侵袭,同时可能在这之后出现禁欲的想法,想以秩序来对抗虚无;有的人因为恐惧虚无而产生自恋,试图把自己当作悲剧主角以感受到忧郁和虚无的美,或是因此产生恋尸或恋童的倾向,以感受自身的生命力或是他们的纯真。对虚无的感受由此可能是不真切的,认为自己和虚无言和的人可能正在挣扎,或是相反的情况,克服虚无只能是在心中不断建立栖息地,中间任何一个时点的意义都有可能被推翻。就像楼上说的,西西弗斯推石头确实是很好的例子,必须认为他是幸福的。
百度小说人气榜
扫二维码下载贴吧客户端
下载贴吧APP
看高清直播、视频!
看高清直播、视频!
贴吧热议榜
- 1甲亢哥大张伟终极Boss战将开打1541610
- 2美国50万人游行抗议特朗普1080540
- 3甲亢哥的逆天翻译被央视打码1011416
- 4吧友爆料苏丹的游戏幕后推手796932
- 5新三国离谱程度同人小说都拍不出来559312
- 6向鹏强势横扫李尚洙夺冠438750
- 7小米15S Pro要来了403800
- 8雷军社媒发声不提SU7车祸383525
- 9稻米造血是什么黑科技363572
- 10国内制作组的信任滤镜碎了330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