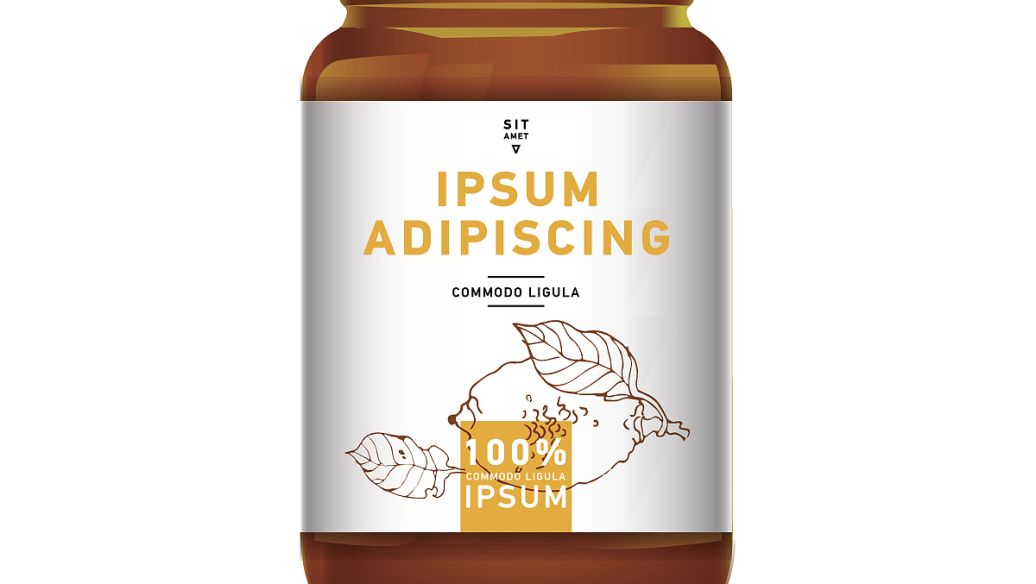中西合璧吧吧 关注:378贴子:152,970
《喝豆汁》韩少华
记得前年去拜望胡絜青先生,言笑间佐不过些居家过日子的常情常事。也不免说起旧时京里小吃,如焦圈儿,薄脆,吊炉马蹄儿烧饼之类。当然也少不了豆汁儿。
"不喝豆汁儿,算不上北京人。"絜老说着,竟敛了敛笑容,"几回家里来了洋先生,东洋的西洋的全有,我就备了豆汁儿款待他们。心想各位没一个不以热爱北京,敬重老舍自诩的,那就尝尝这个,验验各位的诚心得了——老舍可是最好喝豆汁儿了……" 说罢,老人竟屏住了漾到嘴边儿上的笑意。接着说的诸如"焦圈儿"又叫"油炸鬼",跟"薄脆"都吃的是个火候,以及"马蹄儿烧饼两层皮",不是吊炉烤的不鼓肚儿,夹上焦圈儿算"一套儿"的话题,我虽生也者晚,倒还搭得一两句茬儿。而如今,这些东西即便弄到了,焦圈儿不焦,薄脆既不薄且不脆,"马蹄儿烧饼"也不鼓肚儿的情形却常见,则与老人同感。
关于豆汁儿,絜老却并没再多说什么。转年夏景天儿,陪絜青先生及舒乙学兄等家里人,去京西八宝山为老舍先生灵盒拂尘。在灵堂阶下,又听胡先生说起几位健在的老友,说起冰心先生,还随说随叮嘱我:"从文藻去世,她是难免有些寂寞的,你得空儿倒该去陪她说说话儿……"入秋之后,去拜望了冰心先生。还带去了一些麻豆腐。
冰心先生本属闽籍。虽自少年即随父入京就学,但如麻豆腐之类京味儿食品能否入口,我却说不大准,就连同是久居京里的臧克家先生,也曾一听"豆汁儿"就忙皱眉的;而这"麻豆腐",正是豆汁儿的浓缩物。北京土著人士大部知道,所谓豆汁儿,麻豆腐,纯属下脚料。甚或称之为"废料"也没什么大不可。那原是制粉丝,粉皮儿的剩余物,麻豆腐即湿豆渣,而豆汁儿,即豆泔水罢了,早年大凡开粉坊的,总兼设猪圈,以渣及泔水饲饮之,则肥猪满圈,作坊主也易饱其囊。此种经营体制,实属两利。而外乡人或许望文生义,把"豆汁儿"误认为"豆浆",忖度着该是宜甜宜淡的呢,殊不知才舀到碗里,还没沾沾唇,就不得不屏气蹩额了。有扔下钱转身就走的,也有不甘心而憋下口气只咂了半口,终不免逃去的。事后多连呼"上当",甚至说"北京人怎就偏爱喝馊泔水"云云。本来于美食家那里,总讲个色,香,味。而麻豆腐也罢,豆汁儿也罢,却一无可取。
记得前年去拜望胡絜青先生,言笑间佐不过些居家过日子的常情常事。也不免说起旧时京里小吃,如焦圈儿,薄脆,吊炉马蹄儿烧饼之类。当然也少不了豆汁儿。
"不喝豆汁儿,算不上北京人。"絜老说着,竟敛了敛笑容,"几回家里来了洋先生,东洋的西洋的全有,我就备了豆汁儿款待他们。心想各位没一个不以热爱北京,敬重老舍自诩的,那就尝尝这个,验验各位的诚心得了——老舍可是最好喝豆汁儿了……" 说罢,老人竟屏住了漾到嘴边儿上的笑意。接着说的诸如"焦圈儿"又叫"油炸鬼",跟"薄脆"都吃的是个火候,以及"马蹄儿烧饼两层皮",不是吊炉烤的不鼓肚儿,夹上焦圈儿算"一套儿"的话题,我虽生也者晚,倒还搭得一两句茬儿。而如今,这些东西即便弄到了,焦圈儿不焦,薄脆既不薄且不脆,"马蹄儿烧饼"也不鼓肚儿的情形却常见,则与老人同感。
关于豆汁儿,絜老却并没再多说什么。转年夏景天儿,陪絜青先生及舒乙学兄等家里人,去京西八宝山为老舍先生灵盒拂尘。在灵堂阶下,又听胡先生说起几位健在的老友,说起冰心先生,还随说随叮嘱我:"从文藻去世,她是难免有些寂寞的,你得空儿倒该去陪她说说话儿……"入秋之后,去拜望了冰心先生。还带去了一些麻豆腐。
冰心先生本属闽籍。虽自少年即随父入京就学,但如麻豆腐之类京味儿食品能否入口,我却说不大准,就连同是久居京里的臧克家先生,也曾一听"豆汁儿"就忙皱眉的;而这"麻豆腐",正是豆汁儿的浓缩物。北京土著人士大部知道,所谓豆汁儿,麻豆腐,纯属下脚料。甚或称之为"废料"也没什么大不可。那原是制粉丝,粉皮儿的剩余物,麻豆腐即湿豆渣,而豆汁儿,即豆泔水罢了,早年大凡开粉坊的,总兼设猪圈,以渣及泔水饲饮之,则肥猪满圈,作坊主也易饱其囊。此种经营体制,实属两利。而外乡人或许望文生义,把"豆汁儿"误认为"豆浆",忖度着该是宜甜宜淡的呢,殊不知才舀到碗里,还没沾沾唇,就不得不屏气蹩额了。有扔下钱转身就走的,也有不甘心而憋下口气只咂了半口,终不免逃去的。事后多连呼"上当",甚至说"北京人怎就偏爱喝馊泔水"云云。本来于美食家那里,总讲个色,香,味。而麻豆腐也罢,豆汁儿也罢,却一无可取。
先说色。虽系绿豆为原料,却了无碧痕;一瓢在手,满目生"灰",没点儿缘份是谈不上什么悦目勾涎的,在视觉上先就掉了价儿。次说香。因是经过焐沤或口酝酿的,故只可叫做一个馊。当年朝阳门内甫小街儿跟大方家胡同东北角儿开着一家豆汁儿铺。老邻居老顾客戏呼之为"馊半街"。没点儿根基的熏也熏跑了。再说味。既以"馊"为先导,那味可就不只寻常的"酸"了。比如醋,无论米醋或熏醋,临汾醋或镇江醋,都酸得诱人。而这豆汁儿的酸却继馊之后完成着"泔水"的感官效应。难怪除了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能有这等口福的,少见。
记得曾对那出《豆汁记》犯过一点儿疑惑。老戏本子里说金玉奴之父金松,"乃临安丐头"。原来非京籍人士也早有对豆汁儿怀着雅量的。这跟在学问上主张"兼收并蓄"者,似乎都属难能因而可贵之列吧?其实呢,说起京里人嗜好豆汁儿,也没多少奥秘可言。中国有"饥不择食,倦不择席"的老话,西方也有"疲劳是柔软的枕头,饥饿是鲜美的酱油"一类俗语。如果联及旧时曾在东安市场摆过摊儿的"豆汁徐"家内掌柜的所说,京里兴豆汁儿多靠着老旗人的偏好,再联及八旗子弟游手好闲,坐吃山空的背景,以及豆汁儿便宜得出奇还外带辣咸菜丝儿等缘由,那么,所谓"嗜好"或许正是"饿怕了"之故。金松虽被尊为"头儿",可毕竟首先是"丐"。
记得曾对那出《豆汁记》犯过一点儿疑惑。老戏本子里说金玉奴之父金松,"乃临安丐头"。原来非京籍人士也早有对豆汁儿怀着雅量的。这跟在学问上主张"兼收并蓄"者,似乎都属难能因而可贵之列吧?其实呢,说起京里人嗜好豆汁儿,也没多少奥秘可言。中国有"饥不择食,倦不择席"的老话,西方也有"疲劳是柔软的枕头,饥饿是鲜美的酱油"一类俗语。如果联及旧时曾在东安市场摆过摊儿的"豆汁徐"家内掌柜的所说,京里兴豆汁儿多靠着老旗人的偏好,再联及八旗子弟游手好闲,坐吃山空的背景,以及豆汁儿便宜得出奇还外带辣咸菜丝儿等缘由,那么,所谓"嗜好"或许正是"饿怕了"之故。金松虽被尊为"头儿",可毕竟首先是"丐"。
不过,京里也有富贵人家喜好豆汁儿的。听我的老岳丈说,清末叶赫那拉族中显宦,光绪爷驾前四大军机之一的那桐那老中堂,就常打发人,有时候就是我岳丈,从金鱼胡同宅里,捧着小砂锅儿,去隆福寺打豆汁儿来喝。这倒让人想起荣国府里,自贾母以下,那么多人都爱吃刘姥姥进献的瓜儿菜儿的情形来了。那自是膏肥脍腻之余,在口味上的某种调剂而已。或如俗话说的,为的是"去去大肠油",跟"饿怕了"是毫不相及的;至于穷旗人所谓"偏好"云云,似乎也不大说得上,倒让人疑为婉饰之辞。称得起这"偏好"二字的,还真有一位。不过说来有些话长。那是1948年冬。北平停电是常事,戏园子电影院都歇了业,连电匣子往往也没了声音。倒是几处小茶馆儿,一盏大号儿煤油灯往那张单摆在前头的桌子上一戳,再请个说书先生,醒木一拍,就成了书场。朝阳门里南小街路东那家儿,因为离我暂时寄宿的北平二中很近,也就成了我逃避晚自习的去处。
当时在那儿挑灯擅场的,是赵英颇先生。书目自然是《聊斋志异》。四十年代中后期,北平每晚广播里有个压台节日,就是赵先生说《聊斋》。到点之前,不少老北京人在家早闷酽了茶或烫匀了酒,静候着了。记得业师郭杰先生说,烫下酒宁可没卤鸡膀子五香花生豆儿,也不能没"赵《聊斋》"。更多的听主儿是累了一天,盼到晚上,借着一壶酽茶,避入别一个鬼狐世界里去偷个喘口气儿的空隙,可一停电,就连那另一世界也陷到无际的浓黑里去了。这才引出郭先生命我陪他来到这小茶馆儿里听书的事情来。居中一盘小号儿桶子灶。灶口上半压着两把圆提梁儿高庄儿黑铁壶。水汽慢慢蒸腾着。或许满屋子纸烟味儿,都让这水汽给调合匀了,座间该咳嗽的才没怎么咳嗽,要喘的也没大喘。一双一双的眼睛盯着前头,见桌子上那盏大号儿煤油灯正照着个刚落座的中年人,中等身量儿,发福得可以。小平头儿,圆范脸儿,宽腮帮子高鬓角儿,一副大近视镜,瓶子底儿似的,圈儿套着圈儿。难怪他常这么自嘲着:"在下自幼儿就文昌星高照,'进士'中得早";有时候还饶这么一句:"后来状元没点上,'榜眼'倒是中了——看书得把俩'眼''绑'到书上,哈哈哈……"这晚上只见他从大棉袍儿底襟下头摸出个蓝布绢子包儿来,先取出那块醒木,再咂两口掌柜的给沏好的热茶,才微低着眉目,扯起闲篇儿来。
"今儿这天儿可够瞧的。半路正踩上块东西。什么东西?靴掖儿?里头还叠着花旗股票,要不就是汇丰的现钞?——嗐,柿子皮!多亏天儿冷,冻到地上了。要不介,一踩一跳溜,得,今儿这场'灯晚儿'就非'回'了不可……" 不知怎么了,那晚上听的《胭脂》虽妙趣联翩,可我没记住多少;倒是这几句开场的闲文,一记就四十多年。
赵先生说《聊斋》,或可称之为旧京一绝。据传闻,在鼓楼一家书场,一位老听主儿,还是位"黄带子",当面儿送了八个字的考语,叫做"栩栩如生,丝丝入扣";赵先生正侍立着,登时就冲那位爷抱了抱拳。旁边一位短打扮儿的猛搭了句茬儿,说听您的书,一会儿三魂出壳,一会又送我魂附原身,打发我躺到炕上自个儿慢慢儿琢磨去;赵先生听了,不由得单腿屈了屈,愣给人家请了个家常安。又一位从背灯影儿里冒了一句,说听您的书听一回就跟多活了一辈子似的,把人活在世上的滋味儿都另尝了一个过儿……当时,没等这位说完,赵先生就一把拽住人家袖子,连说今儿这顿夜宵儿我候了,我候了!
赵先生说《聊斋》,或可称之为旧京一绝。据传闻,在鼓楼一家书场,一位老听主儿,还是位"黄带子",当面儿送了八个字的考语,叫做"栩栩如生,丝丝入扣";赵先生正侍立着,登时就冲那位爷抱了抱拳。旁边一位短打扮儿的猛搭了句茬儿,说听您的书,一会儿三魂出壳,一会又送我魂附原身,打发我躺到炕上自个儿慢慢儿琢磨去;赵先生听了,不由得单腿屈了屈,愣给人家请了个家常安。又一位从背灯影儿里冒了一句,说听您的书听一回就跟多活了一辈子似的,把人活在世上的滋味儿都另尝了一个过儿……当时,没等这位说完,赵先生就一把拽住人家袖子,连说今儿这顿夜宵儿我候了,我候了!
扫二维码下载贴吧客户端
下载贴吧APP
看高清直播、视频!
看高清直播、视频!
贴吧热议榜
- 1解放军联合演训释放什么信号2320170
- 2甲亢哥被女coser贴脸歧视1914203
- 3愚人节告白失败成小丑1766772
- 4mujica第三季制作的原因找到了1606149
- 5尹锡悦弹劾案将如何收场1443390
- 6Faker捐款5000万韩元被骂抠门1411350
- 7马斯克的百日维新要失败1384848
- 8藤本树把电锯人那由多写死了1038841
- 981192收到请返航934318
- 10崩铁本期混沌大伙战况如何?872235